本篇文章是由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公报》发表的一篇治理的论文,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“双百方针”,理论联系实际,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,交流科技成果,促进学院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发展,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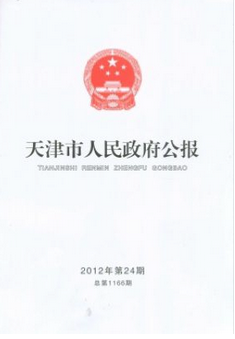
今天谈论的话题是与政府相关——“如何治理中国”,不过我们有个副标题:央地关系的法治化。我把央地关系比作国家的脊柱。每个人有脊柱,国家也有脊柱,这个脊柱就是央地关系。它把中央首脑和身体各个部位,胳膊、腿啊、心脏啊都连在一起。如果一个人的脊柱出了毛病,他问题就大了;如果国家的脊柱出了问题,那么国家肯定是治理不好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从央地关系角度切入,讨论如何治理中国。
央地关系这个题目很大,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。比如说这个哥儿们(薄熙来照)原来大红大紫,最近混得不太好;现在正是好戏连台啊,还在继续上演着。我对中央的决定举双手赞成(现场笑),太神奇了!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,从王立军跨入美国领馆的那一刻就成了一个神奇的国家。他在重庆做的那一套我全都反对,除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抛出的什么民主15条,但恐怕也是欺世盗名的招牌。我是希望地方领导人有他这种个性,但是这个家伙搞的那一套太有欺骗性、太危险,目前多数国人确实容易受骗,所以打得好!不过,这样一来左派不高兴了,说这么做违反程序,他是重庆当地的一把手,应该由重庆人民来决定他的命运;据说他在重庆“唱红打黑”还很受欢迎,中央就这么把他给换掉了。居然还有个北大的说,这是“反革命政变”。这显然离谱了。如果是薄熙来换了胡锦涛,那是政变;胡锦涛换薄熙来,在党内绝对名正言顺。从陈希同到成克杰到陈良宇,中共从来是这一套做法,没听说过“政变”的。
当然,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是另一套治理模式,应该是非常自下而上的,但是宪法管不了党;相反,宪法被党管着,而党内的执政模式是严格自上而下的。所以薄先生落到这样的命运,一点不奇怪,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就奇怪了。我觉得左派朋友需要从这些事情上反思,不要再反对民主、法治,因为独裁、人治这套东西,弄不好搞到自己头上。薄熙来自己在重庆搞的就是这一套。表面上是“民粹”,实际上一手遮天、为所欲为,重庆人民根本不知道他在那儿玩什么。我想随着中央调查的展开,更多的细节不久就会披露出来。我敢断定,他是重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贪官,最大的黑帮首领。重庆的“打黑”实际上就是以黑吃黑,最后就剩下一个黑社会,那就是当地的公权力,黑老大就是他自己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重庆模式”的实质,只是真相都被他掩盖了。我个人从来主张在中国扩大地方自治。在他出事之前,我就说过要让“重庆模式”和“广东模式”自由竞争,中央不要随便插手;他出事后,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。但是良性竞争必须建立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基础上。如果连什么是真正的“重庆模式”都不知道,怎么判断?谈何竞争?他在重庆,有哪个重庆媒体敢说他一个“不”字?全国都没有媒体敢讲他,看来在中央也有他的人。不仅重庆人不敢,北京律师到重庆不照样受迫害?如果哪个南方系的报纸揭露他的底子——当然,这本身就很不容易,因为你要进最大的黑社会卧底多年,敢冒巨大风险才有可能知道底细——他也照样可以来个“跨省追捕”……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,当然是没法搞什么民主的。只有从上面端掉这个黑窝,这是为什么我赞成中央处理的结果。
但是我和左派一样,对这种处理方式不满意。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,不能总是靠这种高度人治化的方式来治理。今天你可以处理一个薄熙来,明天可能有一个“厚熙来”,后来再来一个“厚东来”……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尽头。那真正的治理方式应该是怎样的?在这个问题上,右派和左派的主张其实是一样的:自下而上,不是自上而下。都说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”,我们不应该做“不明白真相的群众”,但我要强调的是,人民的眼睛只有在言论和新闻公开的社会中才有可能是雪亮的,否则大家尤其是重庆市的人民都只能是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。这是我国最近发生的事情,我认为中央可以做得更好,或者在今后应该换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,不该管的事不要管。地方的领导人应该在自由公开透明的环境下,让地方人民自己来决定,中央要做的恰恰是为我们保证一个自由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。
另一方面,中央该管的事情往往没有管起来。右边这张图是苹果和唯冠的争议,是关于IPAD的知识产权。我后来才知道,原告要维权,必须在全国两、三万个地方法院起诉,因为我国的工商执法在全国各地不一样,目前还没有一个机制由最高法院综合起来,下达一个统一判决,后交给工商局让它统一执行,不论是哪种判决结果。这种处理方式会让高度地方自治的美国都忍受不了,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高度的法治不统一。一个地方法院这么解释知识产权,另一个地方法院那么解释,一部法律岂非四分五裂?偌大一个国家岂不要“国将不国”?这恰恰是中央应该管的事,我们却没有管。这两件事表明,央地关系是很重要的治国问题。
当然央地关系出错不一定总是带有喜剧性的方式出现,也完全可能体现为悲剧,甚至极严重的悲剧。中国数千年文明下,最大的一场悲剧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“大跃进”带来的所谓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实际上就是一场大饥荒。大饥荒的直接起因不是什么“自然灾害”,而是中国的央地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在我国按照自上而下层层管理方法,地方永远是听中央的;中央一个指令下来,地方没有抗拒能力。地方官员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,必须迎合上级的指示和命令,甚至有过之无不及。1958年,中国风调雨顺,获得了粮食生产大丰收。1959年,老天爷少下了几滴雨,中央未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,还是照原来的粮食生产指标下达至下级。能否完成呢?当然可以,不然你的乌纱帽还想不想要?不仅要完成任务,还要超额完成任务;让我今年交50万斤公粮,地方就说能交60万斤。所以各地到处“放卫星”,这是毛泽东视察河南郑州(图)。河南是“放卫星”最厉害的地方,饥荒自然也是最惨烈的。中央一听,信以为真,又再加码。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,中央不知道,增加了粮食征购的数量,而地方没有粮,就在老百姓头上克扣,导致全国农村口粮不足。
人是很脆弱的动物,一个星期断粮就可以饿死人;两周没有粮食,村子里的人都会死绝。河南、安徽等农业地区就是如此。当时一个村可能就剩下几个干部及其家属。他们之所以活下来,是因为他们守着粮仓。在饿死这么多人的情况下,某些地方的粮仓竟然是满的。你们在一些电视剧中就能看到这样的镜头:地方发生饥荒,粮仓有粮,官员却不敢开仓赈灾,因为要经上级同意,但等你派信使到北京报告得到批准再回来,当地人早就饿死了。有些好心的官员擅自开仓,是冒着掉乌纱帽甚至掉脑袋的危险的。多数官员当然不敢冒险,所以在饥荒发生的当时,有些地方的粮仓却是满的。只有在一个中央集权国家,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它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交流的失灵。干部之所以能活下来,是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特权偷点粮食出来,便足以养活自己一家老少。
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中央不知道的。有些人妖魔化毛泽东,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,故意制造了这场灾难,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,也模糊了问题的本质。其实你在妖魔化的时候,你也在神化他,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超人,但实际上“伟大领袖”也是可以很无知的。这张图是毛泽东在郑州兴致勃勃地视察田里的庄稼,而当时信阳已经饿死了百万。信阳可不是什么穷地方,素称“鱼米之乡”。毛泽东在信阳事件期间两次去郑州视察,而郑州离信阳才300公里之遥。但是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看着长得非常诱人的麦子,一定感到非常欣慰吧,对300公里之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。所以不要以为“伟大领袖”是万能的,他也有不知道的事情。等他缓过神来知道当地官员骗了他,开始处理这些省委书记、县委书记,可信阳百万民众已经成了地下冤鬼。这是当地饿死人的惨剧,是一个孩子。这类个案非常多,根据一些学者(包括国外学者)的调查,这个数字难以准确统计。我们谴责日本人南京大屠杀,据说死了30万,但是具体数字还是很难调查清楚。大跃进据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500万,国内历史学者所统计的平均数字是3000万,一位在香港大学的英国学者统计“大跃进”包括饥饿其它非正常死亡(比如遭虐待和被殴打致死的)加起来有4500万多人。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统计清楚,但其中有很多个案是极惨烈。比如母亲自己拿到一点粮食,却不敢让孩子知道,因为怕孩子吃后告诉别人家的孩子,这样就麻烦了,结果孩子活活饿死了。在一个极不合理的央地关系制度环境下,毛泽东没有必要是魔鬼就可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。
到今天,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改善了吗?我想大跃进、大饥荒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不会发生,至少希望不会发生。但是表明央地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善。“大跃进”没了,却出来许许多多个“小跃进”。这必然会导致产生很多和“大跃进”性质相同的事件,只不过后果没有如此严重而已,但是央地制度的症结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系统研究了各国央地关系的不同方面,我们尤其关心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央地关系。这儿显示的是我们去年出版的两本书,一是《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》,另外一本是《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》。
首先,让我们来考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理论问题。中国自秦朝以来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央地体制,中央一直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,它被认为掌握了全部国家主权。这种观念首先要修正,所以我们首先考察了国家主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。通过理论研究,国内宪法学者(主要是左翼的宪法学者)对主权概念尤为青睐,其实主权至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,而且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。在宪法研究领域内,主权概念没有意义,因为宪法是国内的部门法,一般不涉及主权问题。只有讨论国际问题,至多讨论一些领土争议,比如南海问题或两岸关系时才涉及“主权”。中国央地关系的真问题不是国家主权问题,而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,为此要搞清楚“地方自治”这个概念和单一制、联邦制之间的关系,因为有个领导人强调“五不搞”,联邦制是其中的一个“不搞”。不搞联邦制是否意味着不能坚持地方自治?通过理论和概念上的研究可以发现,地方自治和联邦制没有必然联系,世界上有一些联邦国家可以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,比如印度、拉美国家,有一些单一制国家可以是高度地方自治的国家,比如法国、英国。虽然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在历史上有过紧密的关系,我以美国为代表,地方自治做得最好的国家也是联邦国家,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必然联系。《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》这本书探讨了地方自治的成本和利益。这个话题本身很大,地方自治有它的成本,中央集权也不能说没有好处,但在我们一贯把中央集权的好处看得过大,过分夸大了地方自治的弊端。所以在这里我主要凸显的是地方自治的利。地方自治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。
首先,地方自治能表达地方偏好。只有通过地方自治,地方人民想要什么才能够充分、准确的表现出来。在这么大一个国家中,这么大的地方差异,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地方代表体制,否则不可能充分准确的反映地方人民的需要。其次,能够促进地方试验和制度竞争。我一直赞成“重庆模式”和“广东模式”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竞争,但前提是必须让当地人民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。随着事件的进展,重庆模式成本会逐步展示在大家面前。在这个基础之上,地方进行不同的试验(无论是左还是右)对中国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中央避免把重庆事件变成路线斗争,而事实上这不可怕,中国各个地方就应该有政策上的多元化和自主性,只要不涉及大政方针,只要当地不宣布独立分裂,有什么好怕的?重庆“唱红打黑”,如果成本和利益都由重庆人民负担,他们拥护“重庆模式”没有什么错,只有通过地方试验才能在全国形成良性的竞争,否则中央只有“五不搞”、“六不搞”,什么都不搞,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带来的好处与弊端?怎么选择治理模式?所以地方试验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制度进步的非常有效方式,和当年1978年小岗村一样。小岗村在后来之所以在全国推广,是因为在当地的试验效果好。当然,也可以搞“人民公社”,河南的南街村据说搞“人民公社”;如果确确实实和对外宣传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“人民公社”,它当然可以存在。只要对人民有好处,为什么不可以?但如果有欺骗,这种模式其实无法维持不下去,完全靠中央某部财政投入给他输血,那么这个真相必须让当地的人民知道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:http://www.lunwencheng.com/lunwen/zfa/10868.html